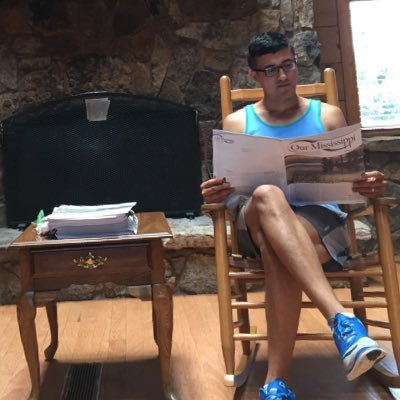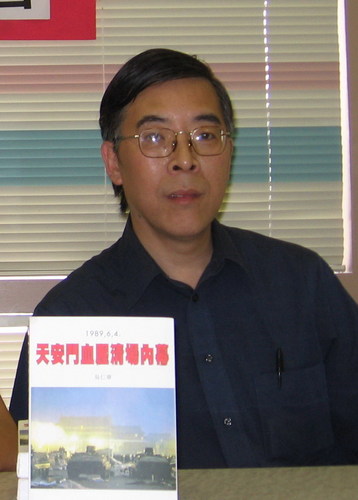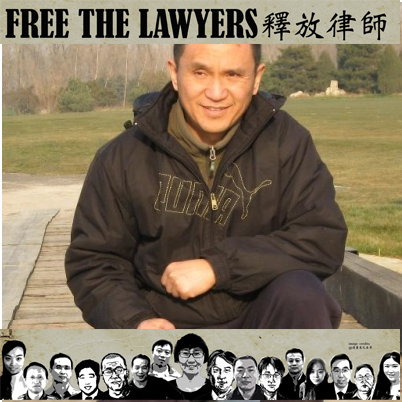吴祚来
6个月前
ZhengXuguang郑旭光
7个月前
勃勃OC
8个月前
五岳散人
8个月前
吴仁华
8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