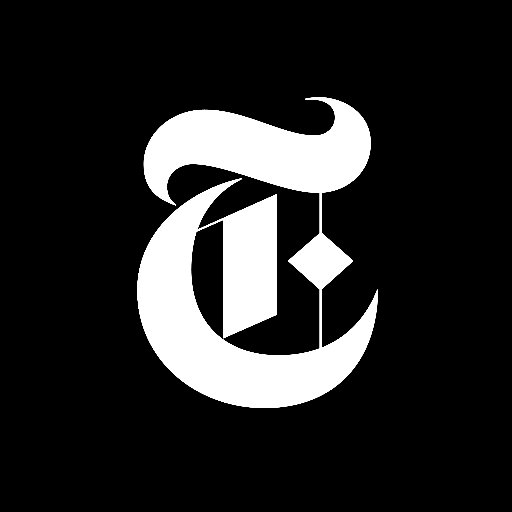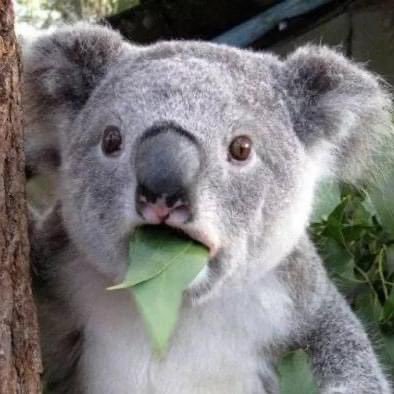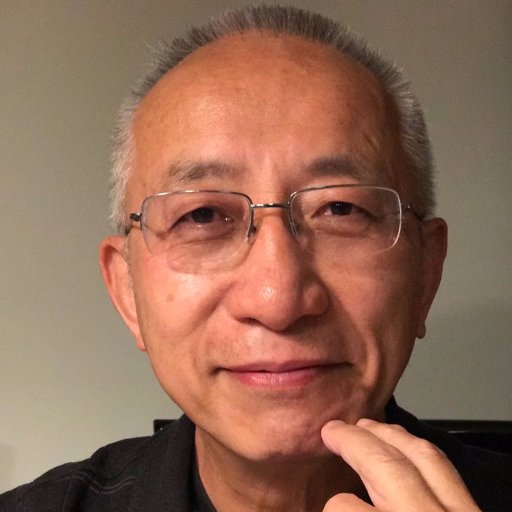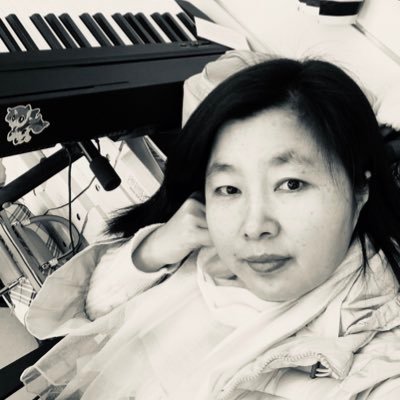佛瑞德里希4th😷
3个月前
小径残雪
4个月前
Ignatius Lee
6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