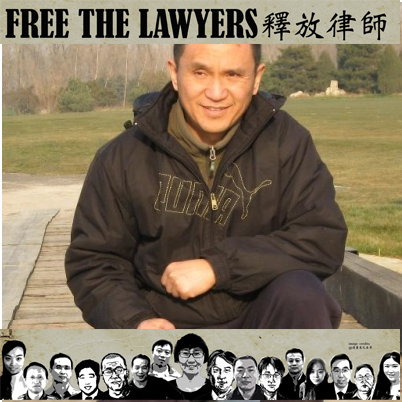Ignatius Lee
6个月前
朱韵和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