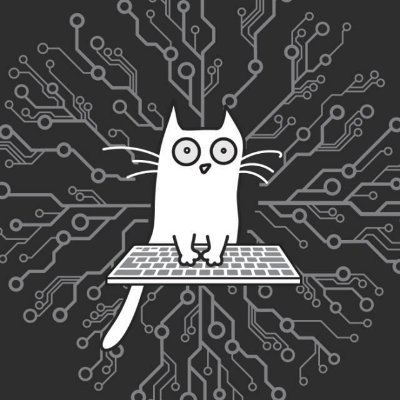Ignatius Lee
2个月前
Ignatius Lee
5个月前
Ignatius Lee
5个月前
Ignatius Lee
5个月前
Ignatius Lee
5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