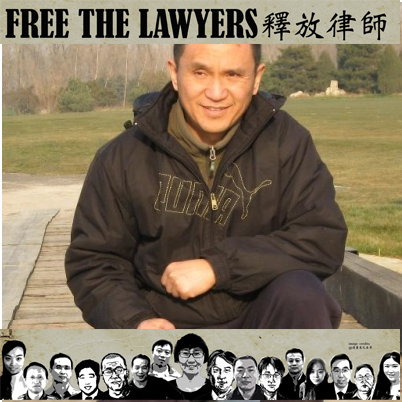朱韵和
统计数据
3478
文章
0
粉丝
0
获赞
191463
阅读
朱韵和
8个月前
朱韵和
8个月前
朱韵和
8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