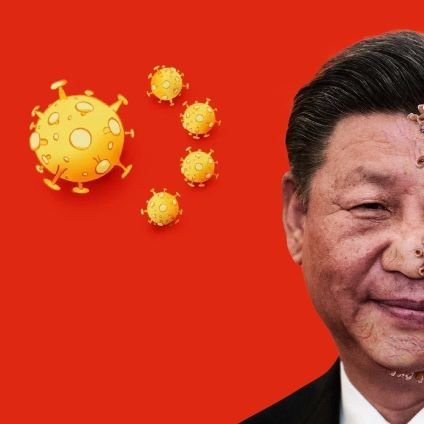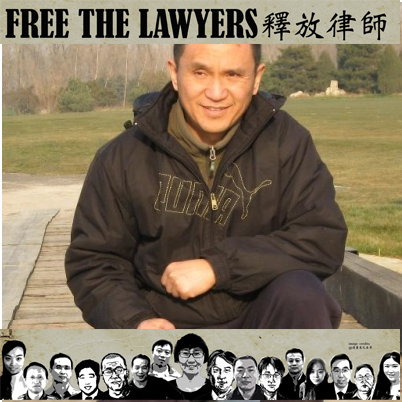周锋锁 Fengsuo Zhou
4个月前
Terence Shen 公子沈
4个月前
Morris
4个月前
朱韵和
10个月前
朱韵和
10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