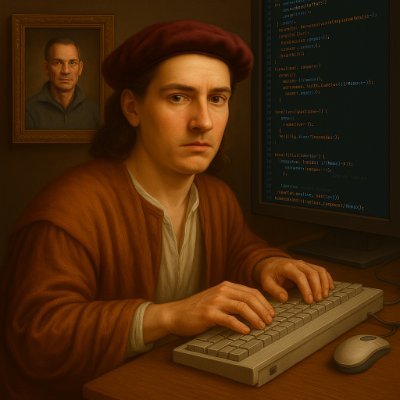𝙩𝙮≃𝙛{𝕩}^A𝕀²·ℙarad𝕚g𝕞
4个月前
𝙩𝙮≃𝙛{𝕩}^A𝕀²·ℙarad𝕚g𝕞
4个月前
𝙩𝙮≃𝙛{𝕩}^A𝕀²·ℙarad𝕚g𝕞
5个月前
𝙩𝙮≃𝙛{𝕩}^A𝕀²·ℙarad𝕚g𝕞
5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