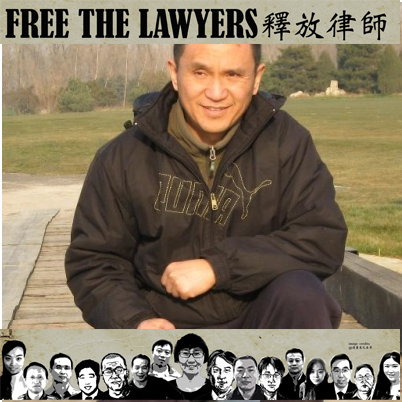程益中
7个月前
Hu Ping胡平
8个月前
朱韵和
8个月前
Guoguang Wu / 吴国光
9个月前
Free Wang Bingzhang
10个月前
Hu Ping胡平
11个月前
朱韵和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