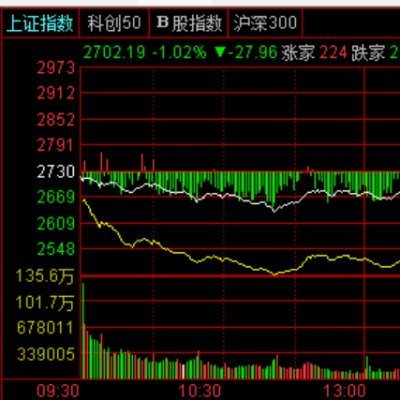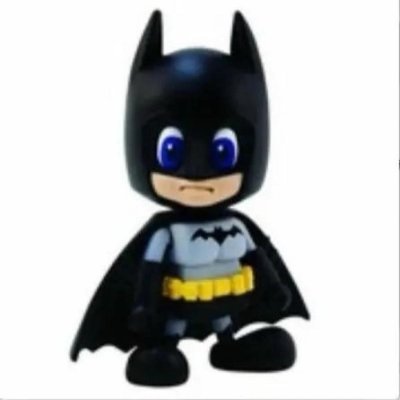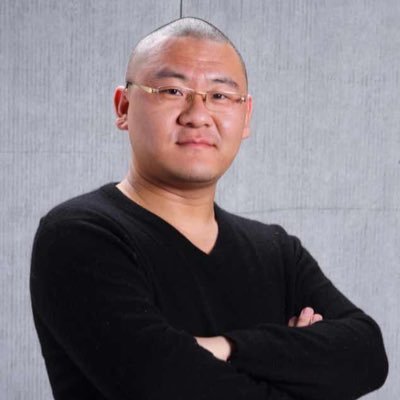Michael Anti
2个月前
XDash
3个月前
Colin Wu
3个月前
ChandlerGuo 郭宏才 宝二爷
3个月前
勃勃OC
4个月前
ChandlerGuo 郭宏才 宝二爷
4个月前
勃勃OC
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