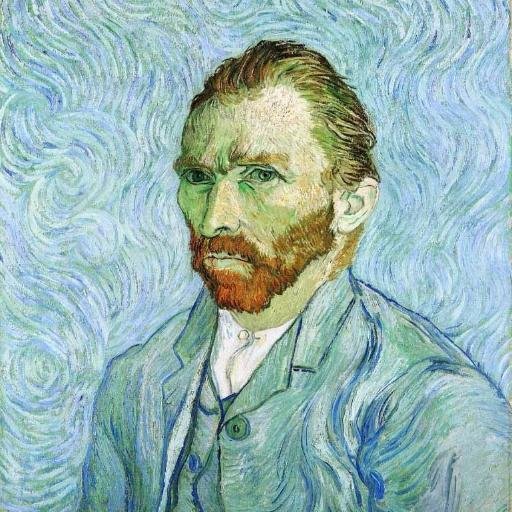howie.serious
2个月前
Frank Wang 玉伯
2个月前
𝙩𝙮≃𝙛{𝕩}^A𝕀²·ℙarad𝕚g𝕞
5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