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浪新闻-新京报
新浪新闻-新京报
5天前
![]() 新浪新闻-新京报
新浪新闻-新京报
5天前
 勃勃OC
勃勃OC
5天前
 Jacobson🌎🌸贴贴BOT
Jacobson🌎🌸贴贴BOT
5天前
![]() 新华网-经济日报
新华网-经济日报
5天前
![]() 网易新闻-中安在线
网易新闻-中安在线
5天前
 Jacobson🌎🌸贴贴BOT
Jacobson🌎🌸贴贴BOT
5天前
![]() 网易新闻-大皖新闻
网易新闻-大皖新闻
5天前
 勃勃OC
勃勃OC
5天前
![]() 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5天前
 LT 視界
LT 視界
5天前
![]() 新华网-央视一套
新华网-央视一套
5天前
![]() 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5天前
![]() 网易新闻-新华社
网易新闻-新华社
5天前
 Weiping Qin 秦偉平
Weiping Qin 秦偉平
5天前
![]() 网易新闻-环球时报
网易新闻-环球时报
5天前
![]() 新浪新闻-新浪网
新浪新闻-新浪网
5天前
 Mr. Owen
Mr. Owen
5天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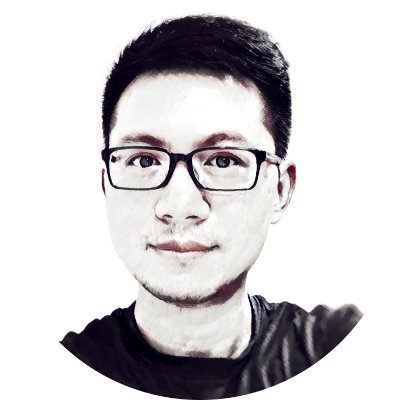 艾森 Essen
艾森 Essen
5天前
加拿大正在成为一个失败国家的底层逻辑和哲学:加拿大实验,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后民族国家”吗?当特鲁多说“加拿大没有核心身份,也没有主流”时,他表达了一种独特的加拿大哲学,10年前很多人认为这或许代表了全新的先进的国家模式,10年后看这就是天真和幼稚,这就是加拿大成为失败国家的核心和根源。 2017年伊始,加拿大或许成为了世上硕果仅存的移民国家。我们的政府坚信移民的价值,大部分国民也对此深信不疑。 2016年,我们接纳了约30万新移民,其中包括4.8万名难民。我们希望他们能成为公民;事实上,大约85%的永久居民最终都成为了公民。 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关于接收单身阿拉伯男性的担忧,但除此之外,加拿大欢迎来自所有信仰和世界各地的人们。 大多伦多地区现在已成为全球最多元化的城市,一半的居民出生在国外;温哥华、卡尔加里、渥太华和蒙特利尔也紧随其后。每年的移民数量约占加拿大当前3600万人口的1%。 近来,加拿大因实际上只是“一切照旧”而受到了过度的赞扬。2016年,包括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波诺在内的各界名流都宣称“世界需要更多加拿大”。 10月份,《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醒目地写着“自由北移:加拿大的世界榜样”,封面插图是头戴枫叶光环、手持冰球杆的自由女神像。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大选之夜,加拿大官方移民网站崩溃了,显然是因为访问量过大。 当然,2016年也是许多西方国家愤怒地反对移民的一年——实际上是连续第二年。他们将移民归咎于各种弊病,正如记者道格·桑德斯所说的,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诉诸恐惧的本能反应”。 伴随本土主义的兴起,一种新的民族主义也浮出水面,它几乎不屑于掩饰其根植于种族认同和排斥性叙事的本质。 与这些强硬立场相比,加拿大近乎乐观的包容承诺乍看之下可能显得有些天真。但事实并非如此。保持开放的大门有其现实的考量。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开始减缓加拿大的自然增长率。十年前,人口增长的三分之二归功于移民。预计到2030年,移民将贡献100%的人口增长。 经济效益也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如果最终目标是完全公民化。所有“定居者”——即非加拿大原住民的加拿大人——只需照照镜子,就能认识到移民故事通常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我们的政府反复强调这一点,我们的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我们自己的所见所闻也印证了这一点:多元化促进繁荣,而不是破坏繁荣。 但除了保持移民国家地位的实际考量之外,加拿大人总体上也天生倾向于一种令他人感到困惑甚至鲁莽的开放性。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在接受《纽约时报杂志》采访时阐述了这一点,他表示加拿大可能成为“第一个后民族国家”。他补充说:“加拿大没有核心身份,也没有主流文化。” 这番言论发表于2015年10月,当时并未引起波澜。但当我向德国欧洲事务部长迈克尔·巴赫提及此事时,他感到震惊。巴赫当时正在加拿大访问,以了解更多关于融合的信息。他说,没有哪个欧洲政治家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个想法太激进了。 对于欧洲人来说,民族国家模式当然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它可能非常不适应边界消融和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时代。 现代国家——大致定义为拥有或多或少连贯的种族和宗教群体,受内部法律统治,并由国民军队保卫——在欧洲成型。告诉意大利或法国公民他们缺乏“核心身份”,可能不是最佳的拉票策略。 但对加拿大人来说,这番言论却平淡无奇。毕竟,加拿大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梅维斯·加兰特曾将加拿大人定义为“一个有合乎逻辑的理由认为自己可能是加拿大人的人”——这并非是对民族性格类型的响亮肯定。 事实上,特鲁多可能是在表达加拿大人长期以来的一种焦虑:缺乏共同的身份认同。 但他并非如此。他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概述了21世纪加拿大的执政原则。我们不常以这种方式谈论自己,也还没有足够的词汇来充分表达我们的观点。即便如此,这个原则感觉是对的。尽管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加拿大可能终于开始正视我们的后民族主义了。 这一切背后蕴藏着不止一个故事。首先,后民族主义是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实验的框架,这个实验旨在用世界的多样性来填充广阔而统一的地理空间。 它也是一项有半个世纪历史的知识分子项目,诞生于加拿大从殖民沉睡中觉醒的时期。但后民族主义在实践中也断断续续地存在了几个世纪,早在1867年加拿大民族国家正式形成之前就已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一直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这片横跨大陆的土地,借鉴了来自原住民社会的思想。 从欧洲人开始抵达北美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并被教导如何在多种身份和忠诚之间生存和发展。 这种欢迎常常遭到背叛,尤其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当时定居者主导的加拿大对原住民造成了深重的伤害。但是,即使这种不平衡依然存在,这种影响也依然存在:另一种归属模式。 任何国家真的能以“后民族”的方式行事吗?——即不依赖既定的国家治理和控制机制? 简单的答案是不能。 加拿大有边境,边防人员在那里检查护照,还有军队。它偶尔也会提出一些适度的领土主张。特鲁多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这些机制:他掌管着它们。 也可以说,加拿大之所以能够享受跳出民族国家框架进行思考的奢侈,要归功于其南部庞大的邻国。 加拿大不必过于强硬地捍卫其边境,也不必让军队规模过大,加拿大的经济繁荣可能仅仅是继续与美国进行75%的贸易。 人们认为,摆脱了大多数其他国家面临的经济和军事压力,这给了加拿大喘息的空间和信心,去尝试更激进的社会模式。我们真是幸运。 在加拿大国内,对于“后XX主义”也并非意见一致。 小说家扬·马特尔曾随意地将自己的祖国描述为“地球上最伟大的旅馆”,他本意是赞美——但有些人却将其解读为认可新来者将加拿大视为一个方便的落脚点:一个安全、商业或房地产机会,而无需承担持久的责任。 同样,许多加拿大人认为我们拥有一套规范价值观,并希望新来者证明他们遵守这些价值观。 保守党领袖竞选人凯莉·莱奇去年秋天建议,我们应该对潜在移民进行“反加拿大价值观”的筛查。前保守党政府的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在2015年承诺设立一条举报热线,供公民举报“野蛮的文化习俗”。 在上届大选中,即将卸任的总理斯蒂芬·哈珀徒劳地试图通过捏造一场关于头巾的辩论来削弱特鲁多的人气。 更复杂的是,法语省份魁北克已经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民族,遍布全国的50多个原住民部落也是如此。他们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优先事项,可能对后民族框架感兴趣,也可能不感兴趣。(尽管如此,特鲁多是一位会说双语的蒙特利尔人,魁北克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多元化社会。) 简而言之,加拿大这个民族国家,虽然不像其他全球版本那样张灯结彩,但仍然是可以辨认的。但后民族主义思想并非是手拉手围成一圈唱歌和撕毁护照。 它关乎于使用不同的视角来审视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挑战和原则。 尽管加拿大自1867年以来就已获得主权,但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仍然笼罩在英国帝国的阴影之下。 直到上世纪60年代,我们才有了自己的国旗和国歌,直到1982年,特鲁多的父亲皮埃尔才从英国手中收回宪法,并增加了权利宪章。他还将多元文化主义确立为官方国家政策。 那时,挑战似乎在于定义一个与之匹配的民族身份。 考虑到我们的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和美国文化的强大影响力,这绝非易事。上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我们不应该为此费心。“加拿大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知道如何在没有身份认同的情况下生存的国家,”他在1963年说过。 诗人兼学者B.W.鲍尔认为,麦克卢汉在加拿大看到了构建充满活力的新型民族国家的原始素材,这种民族国家摆脱了国家的“划定边界线和墙壁,摆脱了与血统和土地的联系”,摆脱了对“基于大熔炉、本土主义热情、应许之地理念的凝聚力的痴迷”。 相反,既有加拿大身份认同的薄弱之处,也鼓励了多元身份认同——更不用说健康的灵活性和对变革的接受能力。 一旦加拿大不再优先考虑前帝国臣民,转而实行多元文化主义,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多种信仰、历史和愿景”可以共存的地方。 事实正是如此。 如果说麦克卢汉没有看到在中国人、日本人、乌克兰人以及后来的意大利人、希腊人和东欧移民的支持下,加拿大在最初的沉睡世纪中是如何发展壮大的,那么在他1980年去世前,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了来自南亚、越南和加勒比地区的移民潮的积极影响。 过去几十年,加拿大的多元化程度日益加深,尤其以来自中国大陆、印度和菲律宾的移民为代表。 其他人也扩展了麦克卢汉的洞见。作家兼散文家约翰·拉尔斯顿·索尔(我工作的慈善机构的联合创始人)称加拿大为“对标准民族国家神话的革命性颠覆”,并将我们的大部分激进能力——“激进”这个词你通常不会用来形容加拿大人——归因于我们对原住民欢迎理念的应用。 “为多种身份和多种忠诚腾出空间,”他这样描述这些扎根于北美土壤的哲学,“为一种对矛盾感到自在的归属感理念腾出空间。” 这一切有多独特呢? 拉尔斯顿·索尔认为,加拿大的实验是“永远不完整的”。在其他国家,像魁北克这样的主权运动可能会导致流血冲突。但在加拿大,除了1970年短暂的暴力分裂主义煽动时期(最终导致绑架和谋杀)之外,加拿大和魁北克一直处于持续的妥协模式,在投票箱中争论,并寻找彼此迁就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拿大不完整的身份是一种积极因素,是推动我们向前迈进、避免流血冲突、保持思考和进化的动力——也许,最终只是对新事物做出反应,而无需恐惧。 我们仍在努力完善语言表达。 那些不欣赏别人告诉他没有身份认同的加拿大人,可能也会对被称为“不完整”国家的公民感到不满。 鉴于2016年发生的事件——美国选出了一位主要政策纲领是修建隔离墙的专制主义者,英国投票脱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控制移民,以及对多元化充满敌意的右翼政党可能很快将在法国等国组建全国性政府——美国和欧洲公民也可能觉得所有关于包容和欢迎的言论都过于虚无缥缈,甚至不切实际。 所有这些原始的民粹主义在2017年都不会消失,尤其是在面对全球范围内史无前例的大量人口跨境流动(无论是否持有签证)这一公认的巨大挑战时,民粹主义会变得更加激烈。 但是,否认、坚守本土主义立场、在应对危机和(不太明显的)机遇方面几乎无所作为、不推动社会进化:这些都是反应,而不是行动,而且肯定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如果评论员认为世界需要更多加拿大是正确的,那仅仅是因为加拿大拥有历史、哲学,甚至可能是物理空间,来进行一些关于如何以不同方式建设社会的必要思考。 称之为后民族主义,或者仅仅是一种新的归属模式:加拿大或许能够在注定艰难的来年提供帮助。 ===== 查尔斯·福兰是一位小说家,也是加拿大公民研究所的首席执行官。

 悉尼奶爸 SydneyDaddy 雪梨奶爸 🇦🇺
悉尼奶爸 SydneyDaddy 雪梨奶爸 🇦🇺
5天前
 徒步的骑手
徒步的骑手
5天前
 谷风
谷风
5天前
![]() 新华网-新华网
新华网-新华网
5天前
 iPaul🇨🇦
iPaul🇨🇦
5天前
 勃勃OC
勃勃OC
5天前
 勃勃OC
勃勃OC
5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