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月前
相关新闻

Didilara917
2个月前
我叫dilara~土生土长的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人~ 关于新疆的问题可以问我~ 不要看那些流亡海外的新疆假维吾尔族内容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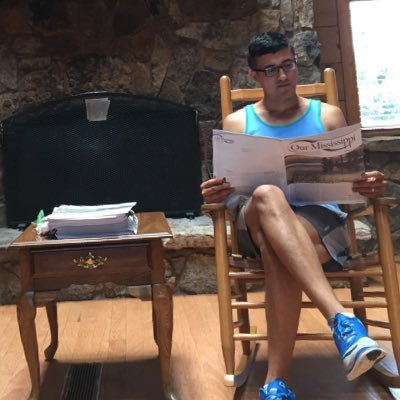
Inty News
2个月前
2014年起,新疆,"再教育营"开始大规模建设。据估计,100万以上维吾尔人被关押,进行强制"去极端化教育"。

Didilara917
2个月前
我叫dilara~土生土长的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人~ 关于新疆的问题可以问我~ 不要看那些流亡海外的新疆假维吾尔族内容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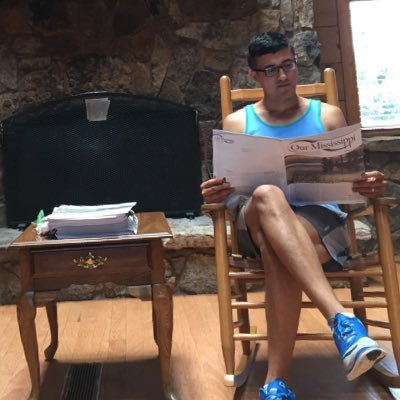
Inty News
2个月前
2014年起,新疆,"再教育营"开始大规模建设。据估计,100万以上维吾尔人被关押,进行强制"去极端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