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月前
相关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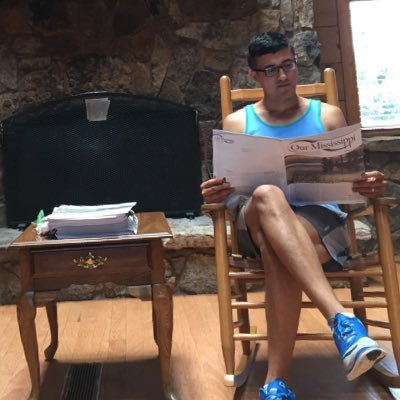
Inty News
2个月前
川普说:乌克兰腐败丑闻“无益于结束战争的谈判”

all over again
2个月前
一些川粪抱怨泽连斯基不愿土地换和平! 说明他们只是无知,不懂历史。 2014年,克里米亚被被侵略,乌克兰用土地换和平; 结果换来普京对顿巴斯的侵略,最后换来对乌克兰的全面侵略。 所以对于普京而言土地真的可以换来长远的和平吗? 如果侵略可以得到奖励,历史证明,这只可能换来未来更大的侵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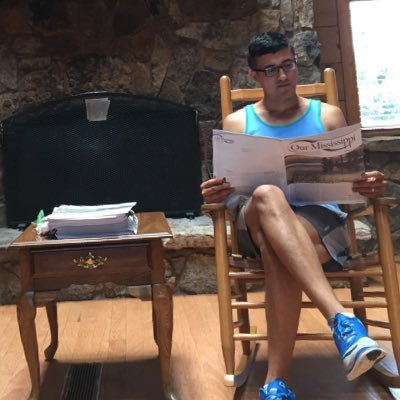
Inty News
2个月前
美国和乌克兰,今天的谈判开始


